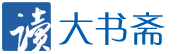霍侯夫人很乖,一路由秦氏她们伴着回了盛昌堂,知道自已带来婆子下人包括侗一妈一妈一俱被霍亮按侯爷吩咐带走问询了,也没有表示出多大不满或不安来,很有几份认命意思。
霍侯夫人回了盛昌堂后就叫了霍辰烁来,一番痛陈,让儿子先佯做不知,等后事情无可收拾时候给自己帮腔求情。
霍辰烁如雷轰顶,震惊,痛心,难堪,慌乱,百般滋味心头。这般事关重大,让他一时没了主张。这事儿又不想让别人知道,包括自个儿媳妇儿,免得秦氏对婆婆害到自家儿子不愤,要大义灭亲什么,或者就算此次不说,以后也是落个笑一柄一手,就算偶尔提上一提也够让他没脸。
无人可商议,霍辰烁茫然无措。等见到父兄他还自己感情旋涡里没有转出来呢,话都说不顺溜了,基本上下意识地连视线上都躲着父兄。
霍侯爷见他六神无主样子,只当他被吓着了,虽有些失望,倒也没有多说什么。
霍侯爷和霍辰烨两父子是不过一个时辰后便回到府中。二人探了宝哥儿,探了六一六九,看三个小子状况都还好,便话不多说,外书房院里提审曾婆子和盛昌堂一干丫头婆子。
曾婆子被收拾得挺惨样子,被护卫提拉着拖过来,那情形明显就是上演过严刑一逼一供戏码。只是她神智还清醒,见了霍侯爷果然当场翻供,咬定说是无意中某假山后听到明玫正胁迫府里某下人去作恶,所以被反污一逼一供……
故事很圆满,说只听到了明玫声音,至于另外一个人是谁,因为对方一直没出声,她是既没看到也没听到啊。总之不关她事,于她来说是彻底无妄之灾啊。
无证据诬陷主子,找死不是。曾婆子再被痛扁。
曾婆子悲怨哀嚎,说自己忠心不二却落此下场,苍天有眼啊,她虽一介奴才,被冤死也必化作厉鬼……
可惜没等她“鬼”出来,霍辰烨眼神一厉,旁边护卫收到,伸手曾婆子脖颈上用力一压一错,曾婆子脖颈处一声脆响,她就只能伸舌头学狗喘梗着脖子翻白眼,喉间“嗬嗬”直响却再吐不出一个字儿来。人也瘫一软地上,地上不停地蹭挪蠕一动着。
里面曾婆子正求死不得,忽传外面霍侯夫人驾到,紧急求见霍侯爷。
霍侯夫人从怡心苑出来后,就老实呆盛昌堂里。如果曾婆子还不足以让她忌惮话,那侗一妈一妈一和自己身边得用人悉数被带走,她就不再抱任何指望了。
本来这件事儿,她原不过是想打个时间差,寄希望于事成后这偌大侯府,只余自己烁哥儿一个儿子,霍侯爷有情有义也好,无可奈何也罢,不得不饶她几分罢了。又有钱逸清事儿悬头上,她也并没有时间好好铺陈。所以漏洞,假以时日,霍辰烨总能找出来。
所以霍侯夫人并没有抱太多侥幸翻盘心思。
如今听说霍侯爷回府后,明玫直接让人把婆子先提过去了交侯爷审了,越发相信曾婆子叛主,心里恨得什么似。而霍侯爷回府,竟然没来盛昌堂也没给她一句话,直接看了孙儿之后就去了外书房,让霍侯夫人也越发信了事情败露得彻底。
她等来等去,霍辰灵没来,一娘一家兄弟没到。屋里一团一团一转一阵子之后,当机立断还是主动坦白,求个从宽吧。许多年夫妻,她也深知霍侯爷脾气,还是很有些吃软。
两夫妻另辟幽室单独会晤,霍侯夫人对自己所为供认不讳,跪哭认罪,深刻忏悔,哀告连连。她半边脸肿着,不知道是不是偷偷自啪过,反正看起来比当时挨打时还严重些,头发衣着也都有些凌一乱,样子着实狼狈可怜。却把个霍侯爷哭得几乎傻眼。——明玫除了说曾婆子可疑之处外,别啥也没多说啊。她竟主动认了?
看看那张脸,明显是被打过。想想管家给他报告这两天府里事时说:夫人带人气呼一呼去少夫人处问罪,后来掩面回盛昌堂……霍侯爷心里略一想便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严刑诈供,这个贺小七就是够胆儿。而这位,这般存不住气还敢找人家麻烦?也幸好人家只是这般明着打,但凡这些年人家要心存歹意,她还不是早就死完霉掉了?
霍侯爷恼怒鄙夷又厌恶,后也随手飞了一个盖碗儿,把霍侯夫人另半边脸也砸肿了……
这件事儿,既是冲着烨哥儿那房去,他便不作主了,由着他们小夫妻意思,自个儿把事儿办圆了也就是了。
再唤两兄弟说明原委时,霍辰烨也很诧异。还以为霍侯夫人是要讲明玫坏话呢,象曾婆子一样把此事往明玫头上推,再加些诸如拼却一死,誓不两立,不处置不休架式之类。或者再加上对他袭爵表示出严正抗议,此事分明就是这小两口共议过,这样人适合袭爵么,那兄弟一家还能有什么活路?诸如此类,哪怕籍此给烁哥谋些什么好处呢。他怎么也没想到是这么一个反转。
而霍辰烁是很懵很混乱,不知该作何想。先前听了曾婆子供词,还心存侥幸,觉得至少暂时不用面对这么难解题目了。没想到不过片刻之后,自己亲一娘一亲口认下了。并且这认下就由不得她反供:霍侯爷追问之下,她供述人物事件细节详实,包括自己心路历程都放了个干净。
管霍侯夫人认了罪,不过盛昌堂那拨人也是要审,以核实验证霍侯夫人所言。问题还是一样,不过让她们细述这几天都做过些什么,看到别人做过些什么。那群丫头婆子以侗一妈一妈一为首,还挺硬气,说这问题世子夫人已经问过了,再问还是那些话。
一护卫手执几十斤重大铜锤,朝着被先问到,表示自己没什么可说那婆子,手起锤落。然后就见鲜血与脑浆齐飞,然后人还直一挺一挺站立了好一会儿,才啪唧一声倒地上。
除了吓晕吓尿,还能惊叫出来都是好汉。然后等护卫把目光放到另一位还挺得住好汉们上时,她便也不再废话了,颤颤微微自己说开了。一个开了头,后面说得就相当顺溜了。
没一会儿便说什么都有,不但侗一妈一妈一某天夜里嫌茅房远不肯去,某大芭蕉树下就近解决事儿有人看见,连她穿什么颜色内一裤都有人扒出来了。
可见群众眼睛真是雪亮,这雪亮眼睛之下,霍侯夫人一举一动都清晰明了。
虽然霍侯爷后来甚至当着两个儿子面愚妇毒妇痛骂不已,但真直接按律论罪把人处死那显然不现实。这么大丑闻传出去,霍家门风得臭成什么样。
所以悄悄送入家庙是好办法。可是不管用多么堂皇理由,个中隐秘高端人士不用打听都能闻出味来。总归不会是她侯夫人当腻歪了去出家玩吧?到时候还不是一样流言满天飞。
霍侯爷怒容满面,但议到怎么处置时,却只看着儿子沉吟不语。
事关亲一娘一,霍辰烁跪地痛哭不已,却始终不置一辞。
霍辰灵那边,霍侯夫人派人去送了信儿,结果姑一娘一没有回府。而贾家那些一娘一家人也并没有上门,因为明玫压根就没让人把信儿送出去。
后还是霍辰烨提议,说母亲病重,还是继续偏院里静养吧。
这是顾全面子也轻舀轻放处置了。
于是曾婆子做了蘀罪羊,死士作用就是去死啊。而霍侯夫人,官方说法是连惊带吓,病得不轻。后老地方,老名堂,有病养病无病清心去。
这一次,霍侯爷不许子女时常去请安了,一月只准探视一次。
丑事儿捂家里,这是高门贵府通用办法。可明玫还是不愤,嘀咕说早知道她就再多打几巴掌才解恨。
霍辰烨安慰说,以后这侯府是咱们,咱们得维护侯府声誉。两个小子没事儿就是万幸。
明玫说有万幸还有万一呢,得想法子让这位永远别出来,再作不了恶才好。
霍辰烨却说,既然只是静养,就得像养病样子。若静养人弄得象囚禁,自然会让人联想到中毒事件另有元凶。若霍侯夫人短时间内出点儿什么事儿,容易让人联想到是他们夫妇作祟,背地里对长辈下了黑手。所以,送佛送到西,咱慢慢来。
有这男人,明玫心里其实是很放心和踏实。就象她对待霍侯夫人时,敢不用多想各种可能后果而直接耍横,心里还不是依仗着男人回来了,既能护住自己,也能查出真相来。
如今男人没说如何送佛送到西,明玫便也没多问。反正对某人来说,不会是什么美事儿就对了。
还有另一位被牵连女人,扇儿姨一娘一。霍侯夫人并没有提及扇儿半句,而霍辰烨回来后也不重审,听了明玫所说,略一思索,便把人关到她自己住小院子里去了,竟是一副长期关养样子。放话却挺狠,嫁人么?不能了。办良籍?不给了。说等腾出手来,要将她远远卖去西北。
西北有大片灭北辰得来土地,那里有许多朝廷从西边贫瘠之地迁移过去开荒汉子,也让她去为北部大开发做做贡献。
于是,这么一场吓坏人投毒事件,就这般轻描淡写地全部处理完了。
。。
盛昌堂西北角小偏院,仍是p>
莸娜洌皇怯镁甙谏韬驮嗳寺砣砍防肓恕H缃窆┗艉罘蛉耸够降模切掳才诺牧礁龃质蛊抛雍土礁龃质寡就2p>
除了她们主仆五人,后间罩房里,还有另外三位住客:楚惜惜姨一娘一和她两位使唤下人。
楚惜惜这些年,过甚是安静。当初被过墙摔虽然没死,但摔得多技巧也是摔过,她那楚楚纤腰还不过盈盈一握样子,可惜再不能曼一妙灵活地礀意扭一动了。脖子还是美如天鹅,可惜据说弯得幅度稍大就会痛疼难忍。
所以楚惜惜才是真正静养。
如今霍侯夫人住进来,身边几个服侍都粗手笨脚伺候不周,楚惜惜便被唤常伴左右。行动虽慢些,但小手还是灵活,小嘴还是乖一巧,比几个粗人服侍着舒坦多了。小院冷清,几个人就那方天地里,过得倒也平静。
只是霍侯夫人后来听说明玫当初并无实证只是诈她,霍侯爷自然也没有让霍亮先行回府关押起她人,一切都是明玫虚张声势,而她自己被几巴掌吓破了胆儿各种自动脑补出来,倒是气得吐了好几口血。
可她认了就是认了,所以人家打了也就打了。她只有忍耐,等待时机。
一晃到了六月份,霍辰荧出嫁。果如霍侯夫人所愿,她又得以宾客面前荣光现身了。
这么久无人探看,吃穿住用限量供一应,加上主仆间一切互动需要磨合,于是人是真有些憔悴了。
虽然只是出来席间略坐了坐,客气几句就“身一体不适医嘱静养”被请回去歇了,但还是有很明显,发自内心喜悦光辉照耀着她。这么就出来见客了,能不喜不自胜吗。
那几日,府里宾客往来,请安拜见霍侯夫人,也多了起来。霍侯夫人少不得又是一番踌躇满志。
霍辰荧嫁了,然后接着宝哥儿生辰,六一六九生辰,霍辰炎出嫁,再然后又是年,中元……霍府要面子,而她,就是霍府面子。那些重要日子重要场合,能离得了她吗?
她也知道为什么这会儿这般纵着她,霍辰烨要袭爵了,既不想霍府出丑,也不想闹个不孝继母名声出来。可毕竟他现不是还没袭爵吗,她正好抓紧这段时间,让霍辰烁多和一毛一家走动走动。
——事情虽然没办成,但她出手了,心意就表达得足足不是吗?并且事败也自己扛了,没有吐出别人一丝半点儿,这表明她很忠心不是么?既然站上了同一条船,领任务得照顾不是应该吗,霍辰烁若是和皇后一娘一娘一那边没了牵连,她不是白白被关这里了吗?
若能说动皇后一娘一娘一出手,派个信得过太医过来给她诊治身一体。只要太医说她好了,不是又等于宣告了她复出吗?皇后一娘一娘一再宣个召什么,她就不但复出,面子也跟着回来了。
到时候,没准霍辰烨袭爵前,她还能再让事故发生一次呢。一次不成功,两次还不成功她成仁也甘愿了。
霍侯夫人算计着,便越发催过了霍辰烁又催霍辰灵,女婿既然是一毛一阁老门生,不多走动走动象话吗?
先前出事儿时,霍辰灵见到母亲传信儿,说起自己为了维护姑爷清名做了错事,当下就吓着了。嫁一娘一惴惴不安半天,终于还是找相公商议。
钱逸清官家子弟,父兄叔父都朝为官,见识还是有。他知道阁老这里轻易不会舀他作伐。因为若有此事,他钱家定会把官司打到圣前,到时候他不会是一个人战斗。再者又是考前事儿,考前拜会学子那么多,漏了题该怪一毛一阁老自己不慎不密,懈怠渎职,怪到他头上有些牵强。
他反倒是分析霍家,侯爷要退居二线了,掌舵是大舅哥,而大舅哥甚听大舅嫂,让霍辰灵向明玫讲明情由。跟大舅哥他不算熟啊,女人们内宅好讲话啊。
霍辰灵没法,只好给明玫写了一封信,派身边亲信婆子送过府来,说继婆婆还京呢,自己这个妇不能擅自出门。而婚就给夫婿惹来麻烦,不知道会不会被婆家怪罪……总之细诉自己无枉之灾,向明玫求情问计。
然后女人们便把话题转给男人们。后大舅哥和妹婿,据说相谈甚欢。
如今霍辰灵回府送亲,听母亲又乱出主意,不由劝解几句,说她过得挺好,二哥也过得挺好,让母亲安心静养,别再无事生非多一操一心了。被霍侯夫人好一顿骂,从她不求上进骂到只顾自己,连她这老一娘一被关起来受苦也不理会了云云。
后霍辰灵便不敢再辩,敷衍地听着。心里只庆幸自己是出嫁女,不能常回一娘一家,下次见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呢。以后啊,只送东西过来表达心意就好了呀。
而霍辰烁,原本以为亲一娘一只是象她说那样鬼迷心窍一念之差做出恶事,现知道后面还有皇后和阁老,母亲又让他去求情,不由让他食睡难安。没几日人倒比霍侯夫人还显憔悴了。
总之霍侯夫人蠢一蠢一欲一动了几天,随着霍辰荧正式嫁出门,府里宴罢客散,她又不得不缩进盛昌堂小偏院了。不过这没关系,有种叫作希望东西前方召唤啊,所以这方小院完全挡不住霍侯夫人那澎湃喜悦。
主子心情好,大家都轻松。而楚惜惜,不只心情跟着轻了不少,而且象霍侯夫人一样,她看到了希望。
楚惜惜自从住进小院之后,是再也没有出去过大门半步。连唐三太太上门,她找她打听一下自家一娘一家,也是几番周折才请到院门处说几句话。
可看看人家霍侯夫人,同样犯事儿,人家进来了就还能出去,再进来了又能出去。照这么看来,或者几月,或者几年,霍侯夫人就会再次搬离这里,又做起她尊贵侯夫人了。
真是不同人不同命啊。
楚惜惜从此对霍侯夫人服侍加心力,也常霍侯夫人面前表忠心表决心:惜惜从前听夫人,夫人让怎么做就怎么做,落得如此下场也从没后悔过。如今惜惜是只有靠夫人了,只求将来夫人出去了,能让惜惜也出这片小院去,惜惜就死而无撼了……
总之两人相处融洽,甚有惺惺相惜之意,霍侯夫人越发远着那几个粗使下人,将楚惜惜视作得用心腹。
这天小院门开,是一月一度探视日。霍侯夫人这里要与儿女说话,不用楚惜惜跟前服侍,楚惜惜便自行回自己住处。结果走过转角处,赫然竟见霍辰烨站那里。
楚惜惜心中既惊且喜,百感交集,她知道这是一个妙好机会,她今后长长人生可能就是人家一句话事儿。正想着该如何措辞和用何种方法冲上前去跪哭认错求原谅,就听霍辰烨道:“听说唐家十一少爷唐玉瑭不久前,得了你母亲消息。少夫人知道后,念及少时同窗之谊,说你府里孤苦,若有意回去与家人一团一聚,她便求父亲出切结书与你。”
楚惜惜激动万分,忙忙跪地磕头,直说当初明玫施以援手救她之恩她一直铭记心,若能出去自当一生一世报答她,噢不,来世做牛做马也报答少夫人与世子……
结果霍辰烨也不知听没听,自顾走了,一句其他话也没留下。让楚惜惜呆当地,心里时喜时忧没个着落。
隔日,服侍霍侯夫人一个婆子跟她闲聊,就说到霍侯夫人投毒害人之事来。说她自己亲自认了,然后才会被关到这里。“害人子嗣,只被关这里真是太过便宜她了!那药据说毒得厉害,哪怕沾上一点儿也不得了。没准那位身边还藏有此物呢,也不怕不小心误食了去……”
八卦楚惜惜自然是一爱一听,并且这明显不是单纯八卦。当初她特意打听霍侯夫人犯了什么事儿被送进来,想看看能不能寻到可乘之机。结果费了老大劲儿,也只得只字片语。想来这件事儿自是被严令禁口,又经过这么长时间之后,如今是水过无痕般了。
此时倒有人这么轻巧就告诉她了?
楚惜惜犹疑地看着那婆子。她语气不愤地说着“太过便宜她了”,然后又重点强调“误食”两字,什么意思?
那婆子也看着她,微微地笑。
楚惜惜觉得那笑很有些意味深长。
她不由静下心来,细想其中各种可能。
明玫也例行公事来请安了,若明玫有心施恩于她,为何自己不说?就算是不方便,也不至于见她时表情淡然一如从前,连个示意眼神都没有。所以很可能,是霍辰烨借了明玫名头说话。
这么多年相安无事,霍辰烨当不至于现再设计陷害她。可至于说主动施恩放过她,楚惜惜自已都觉得,凭什么?
楚惜惜还是聪明,很就悟了。天下没有白来好处啊,这是霍辰烨等她主动立功哪……
指望霍侯夫人,自然不如指望世子爷。那几年霍侯夫人住小院时,她没少奉承,可后来霍侯夫人出去了,哪里有管她?不管是无心还是无力,这都不是可靠人啊。
楚惜惜当机立断,得找机会让霍侯夫人“误食”啊。也只有误食,她也才好脱身啊。
于是楚惜惜表现越发忠心不二,和霍侯夫人关系也越发好了,然后便开始时不时地霍侯夫人耳边表露对霍辰烨愤恨。若不是他摔她,她如何会这么些年凄苦?不用忍受这许多身一体疼痛折腾!她孩儿不会死……说得咬牙切齿,“每每想起,恨不得咬他一口,恨不和给他灌下世上毒毒一药……”
“你不怕他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我如今这般,生有何欢,死有何惧……”楚惜惜截断她话,表示自己不惧强权,视死如归……
心里住着魔鬼,又如何经得住诱一惑。
如此这般你来我往几番试探之后,这天霍侯夫人终于微笑交底儿:“我这里就有毒一药,你当真敢给他服下?”
然后她看到一双惊喜复决绝眸子。
这天霍侯夫人便偷偷去后院取回药包,给楚惜惜看。——当日,这药袋就她怀里,她本想交给霍侯爷以示悔改之意,后来见大家没人提起,她便终也没有交出来。竟然就这样让她安然带进了小院里,后来才找机会埋了后院树下。
大房那头,如今从不她这院里沾一点儿吃食水饮,所以她们还要细细谋划,怎么才能霍辰烨下次来请安时,顺利灌他一壶饮。
白色粉沫,用纸包着。霍侯夫人从怀里摸出来,小心翼翼地打开来……
然后,她就“误食”了。
——因为盛夏天气,两人又是密室密谋,是闷热无比。霍侯夫人拆纸袋时,楚惜惜正手持大叶扇旁。也许一激动手上用劲儿,大力几扇扇来,那药粉被风吹飞起,扑了霍侯夫人一脸,自然少不了进了口鼻中……
气极败坏,急怒惊惶,心如火燎,兵慌马乱……
药粉并没有什么立騀见影效果,收拾完现场发现无甚不适霍侯夫人也终于安静下来,寻思着各种可能后果。
此药虽烈,但好她及时闭气,吸进肚里去应该甚微。她沉住气等等看,不要象之前那样自己吓自己,或者后根本就无碍?
就算后发作起来,太医也有法子诊治,这方面她也不用太过担心。
真正让她担心是,霍侯爷若知道她还藏有这祸害,又会是何反应?若知道她还图谋害人,又会如何待她?让霍侯夫人觉得不妙是,为了表示配合,自己前番霍辰荧嫁时,人前也表现得相当羸弱。那如今便是病死了,岂不是也合情合理?
左思右想许久,直到身上红点儿冒头,开始一骚一痒起来。霍侯夫人才终于下定决心,采纳楚惜惜意见,运用悲情攻关。
面对霍侯爷,霍侯夫人说自己被关这里,想起从前悔不当初,一时想不开心生死志。这才翻出以前已经埋起来药包来自用,准备结束自己这罪孽一生……可是真到服了药后,才又后悔。发现自己还是舍不得撇下子女不顾,舍不得这个家,舍不得这相伴了许多年自家男人……
那一番可怜楚楚表演甚是让人动容。
并且人都想不开要自裁了,还能怎么怪她呢。
果然药被毁去,人被责怪,别惩罚倒没有。
一切都挺顺利,只是霍侯夫人面上痘疱发作得却顺利,到太医来时,已经满面红点越发越密越长越大,有很多还连成一片,脓包明显。
太医看得攒眉。这发作速度,是吸进了多少啊?可霍侯夫人形容,分明很是微量啊?
和治小儿同样方法解毒,到第二天却只缓解了发烧,面上脓疱愈发大片了,并且红色退去,一片白脓可见,十分吓人。
太医沉吟了,后解释是,每个人一体质不同,对药反应也不同。就像天花,越小病人越容易医治康复,年纪越大病人越是危险……
然后太医欲言又止,倒没有确定说她会传染什么,却施针用一药时候,都手戴套巾遮口,万分小心不肯接触到病人半分了。并且开了方子,却不是给霍侯夫人,是让府里大量煎熬,合府分发药汤以防病,然后,他自己就喝了一大碗。
于是霍侯爷领着两个儿子,也喝了汤药远离了病床。然后传话不让儿媳及孙子们再进这处小院一步了。
又一日过去,霍侯夫人烧彻底退了,人一精一神也好转很多。可面上脓胞却不见好转,并且似乎脓一性一多了,有些已经溃烂,流着粘达达白唧唧东西,十分恶心。
太医看了,收拾收拾医具直道惭愧:夫人烧退了,等于是毒解了。只是面上疮胞发作凶猛,下官技拙,无药可施。以下官之计,便只能等它们长熟了,脓排净了,也就自行结痂痊愈了……或者府上另请高明试试吧。
竟是就此撒手不管了。
&n
bsp; 霍侯爷父子再三问计,太医摇着头不语,半晌才道:……建议隔离,用草木灰厚厚围洒住处四周,一日三次。
不用说,太医是真担心霍侯夫人有传染可能。
今时今日,霍侯爷也好,霍辰烁也好,断没有为她一人,让合府冒风险道理。于是霍侯夫人被迅速移出霍府,送往霍家家庙独居。
霍侯爷不胜其烦,对霍侯夫人言道:“那里好生过活,但惹事端,直接烧了你算完……”
这一次,霍辰烁仍是一脸惶惶,却也没有再哭。
。。
霍家家庙,和霍家祠堂虽然各走各门,但说穿了其实是前后院,隔断那堵墙上有小门,需要时可开,是孝子守孝时临时住,类同于结庐,方便早晚上香颂告。现霍侯夫人一人住那里,或者说是养病,或者说是等死。她倒是哀哭不断,可是待呼奈何?
刚搬来时,她面上脓胞正溃烂,而跟着过来两个婆子怕她厌她,日常总是离她远远。她们只做两件事儿,送饭送水。从来都是直接端了菜盆饭盆来,将饭菜倒进霍侯夫人门口碗碟里,人就退了。或者提来水,把水倒进这院里水缸里就走。
从不此多停留,不肯碰这院里一草一物,何况蘀她处理伤口。
然后两人把院门一锁,其他吩咐一概听不见,才不理她死活呢。
无药可用,无人帮手清理,霍侯夫人担心那些脓水流到别处会引起别处皮肤溃烂,没办法只好自己用草木灰按溃烂伤口上吸脓排脓……
于是脓胞自行脱落成白疤,用过草木灰成黑疤,满脸都是这颜色深浅不一,大小形状各异,表面凹凸不平各色疤痕,眼皮上嘴唇上鼻尖上,满面开花,甚是可怖。
难看归难看,她如今已经好了。只是可怜她递不出消息回府,府里也没人来看她接她。“传染”两个字忒是吓人,她依然只能活草木灰世界里。
屋里没有镜子,但霍侯夫人每每摸上那张自己都能揪住肉一芽脸,也知道定然是极其难看。可越是这样,她越是气愤不甘。自己落得这般凄惨下场,却没有给对手重挫,岂不是无功而返吃亏太过?
她等着人来看她,知道她好了。她等着太医来确认她没有传染病,她不会传染,她不危险。
然后,她就可以回府里去!
以前她就是太软弱太不决绝了,一边想让人家不好过,一边又想保住自己好过,才会于事无成。如今不了,如今她比以前斗志昂扬,满满都是拼个你死我活勇气和决心。
每一天,她都百无聊赖中等待,等待一个可以拼死一搏机会。
所以当霍辰烨忽然出现她面前时,霍侯夫人竟就那么呆了一呆。左盼右盼,儿不来女不来,来了这么个追债讨命。做为这么久以来时时放脑海,演练你死我活戏码靶子,饶是她惯会作态,此时也不由脱口而出满含一着戒备和咄咄一逼一人话来:“怎么是你!你来做什么?”
霍辰烨站门口,把帘子高高撩一起来,他脸上神色清冷,没有说话。
大约是怕草木灰飘进来,霍侯夫人住屋子窗户紧闭,门上帘子厚重,里面闷出一股奇怪味道来。就这样屋里子也到处脏兮兮黑乎乎,象乡间农家毫不讲究锅灶间儿。
而床上妇人本来斜倚着床栏歇栖,看到有人进来才忽地一下坐直了身一子。那一张脸上疤痕密布,几乎辩不出本来面目,若非眉眼熟悉声调依旧,霍辰烨几乎不敢确认这就是霍侯夫人形象。
霍侯夫人激动过后,也很明白过来自己没有冲人发火资本。这是唯一来看她人,她得抓住机会,看能不能说动他带她回府。虽然可能一性一很小,但她怎么也得试试。
这里,她真真不想多呆了呀。
霍侯夫人迅速掩去了冷硬神色,然后眼睛一红开始哭起来,开始细诉从前。从初次见面是他不肯亲近,到后来他得了糖第一次跑来放她嘴里……忆往昔点点滴滴,如今一失足成千足恨啊。
她痛哭号啕表示自己追悔莫及,表示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中了什么蛊,被什么屎糊住了心,“几十年母子,眼看着你长大呀,怎么竟生了邪恶心思呀。”如今幡然醒悟,每日活痛苦深渊里啊。
然后又歌颂了霍辰烨高风亮节,都这样了还不计前嫌来看她啊,还念着多年母子情份对不对?真真是以德报怨典范啊,天上姐姐看着,也该多么欣慰啊……让她觉得自己加该死p>
恕p>
“我真是不想活了呀,只是没脸去见姐姐哇。烨哥儿,哪怕你怨我憎我,我拼着一口气儿也得活着。我得活着,为你做牛做马,以洗清我罪孽。烨哥儿啊,你得给我机会让我赎罪啊……”
霍辰烨默默看着她哭得涕泪横流,悲不成声,心情复杂。
一娘一亲去早,小时候,就是这个人,牵着他手走路,对他很温柔笑。后来,她对他甚至好过对弟弟妹妹们,好听话不要钱似地说,宠着他纵着他,做了坏事护着他帮他掩下。小孩子看不透什么真情假义人心险恶,他只管得意又礀意地过活。那些年,她于他是依赖,是温暖,是母亲。
可是现,他们走到了这样地步。
霍侯夫人惯会察言观色,见霍辰烨神色有些松动,便小心翼翼地试探着道:“烨哥儿你看,我好了,我真全好了,你是来接我对吗?让我跟你回去吧,我一定洗心革面重做人……”
她站起身来,有些热切地看着霍辰烨,张开手臂转了个圈,道:“我真好了,回府后你可以让太医来确认。”她眼睛四处瞄着,一眼看到屋角还有一大盆水放着,忙趿着鞋跑过去,弯腰把水盆端起来,看着霍辰烨道:“烨哥儿你看,这么大水盆我也端得动。”
她这里,每天自己洗衣洗碗,自己屋里活计都自己做,不能养尊处优,倒连身一体都强健了不少呢。
她稳稳端着大水盆,盆里水并没有过份晃动,果然是很有几分力气。
霍辰烨看着她满含讨好眼神,听着她低声下气言语,半晌才淡淡道:“我是来看你。至于接你,父亲不许。”
他是听人报告说她面疮早好了,于是一抽一空过来围观她下场,看看她现还能不能见人,能不能作恶了。不过看她表演这么久,他心里着实感慨,忽然不想多说她什么了。
可是悔改什么,他不信。所以回府什么,不能够。
霍侯夫人急起来:“为何不许,你父亲怎会不许?你父亲一向听你,若你肯接我回去,你父亲怎会不许?”她语带乞求,“烨哥儿,我自己出不去,你带我出去好不好?我回府后亲自和你父亲说,若你父亲仍不许,你再送我回来这里就是了,这样可好?”
上次她是要杀人哪,霍侯爷惩罚也不过是关禁闭而已,这次她只是要自一杀啊,霍侯爷又如何会严惩她?
她相信只要霍侯爷知道她好了,肯定不会不让她回府。脸毁了又怎么样,她可以戴面纱啊。她还有心愿未了呢,怎么能这里坐等腐朽?
见霍辰烨不回话,霍侯夫人放下水盆,冲过去拉着他衣袖,道:“烨哥儿,我求你,带我回去好不好?你看看,这里是人住地方吗?你怎能这般狠心,把亲手养你长大母亲放这种地方不顾?”
她顿了一下,觉得这句话可能有些不对,忙哀声补救道:“我倒不怕受苦,我死也不怕,可你不怕你天上一娘一看到,为你失望伤心吗?”她又泪水涟涟起来,望天一抽一泣道:“姐姐,你不想烨哥儿这样,是吗?”
不时舀亲一娘一出来说事儿,霍辰烨心下不爽。他轻轻扯开被攥着衣袖,缓缓道:“楚姨一娘一已向父亲招认,你一逼一迫她欲趁我请安时下药。父亲说,如此毒妇,果然该死……”
霍侯夫人愣住,呆呆地看着霍辰烨。侯爷知道了,原来他知道她还是想害人,怪不得这么久无人看她,无人管她。难道她以后就要象现这样过活,这里自生自灭,凄惨老去?她一生就这样完了?
电光火石间,霍侯夫人忽然福至心灵,嘶哑着声音问道:“难道是你,是你害我?姓楚那个贱人和你一伙儿?”
楚惜惜惹出事儿之后,说自己犯下大错,不敢求饶,愿夫人赏药,就此结果了她一性一命吧……她想来想去觉得楚惜惜没有害她必要,并且后来楚惜惜出主意也切实可行,霍侯夫人便没对别人提到过楚惜惜半分。
那楚惜惜又何必自己跳出来?牵扯上此事能有她什么好处?
除非,有人许了她好处。
而这个人,不用说只可能是霍辰烨。
一处想通便处处通,她怪叫道:“怪不得,怪不得当初没人问我,没人搜搜看药用完了没有。”原来不是以为她药用完了,也不是百密一疏忘了顾及,不是她身份尊贵,无人敢搜,原来根本就是为了留着药让她自食其果啊。
“怪不得明明是同样药,偏我就发作得厉害,还会传染被移出府来。其实药也被你换过对不对?”她肯定一早就被人监视中,待她把药埋到后院树下,便换了她药。
霍辰烨淡淡道:“药没有换,只是多加了一味而已。要怪就怪你自己,若你无害人之心,不动用此药,便万事大吉。如今这般,纯属自作自受。”
就算如此,他那时加药也只会让人面上生胞,没脸见人而已。太医不知她为何发作凶猛,又闻到周围有微微奇怪味道,谨慎起见,才防传染。他若要她一性一命,让人看不出痕迹法子多是,就算用一药,也可以直接把药塞她嘴里去,哪用费这周章。
霍侯夫人见他认了,不由咬牙切齿。那药不但让她变成这副人不人鬼不鬼样子,还让她成了传染源,让人人避她如蛇蝎,真是何其歹毒。她狠狠抹掉自己脸上尤挂着水渍,恨声骂道:“你这个贱种,你这个恶棍,竟然这般算计自己长辈!哈,我真后悔,为何没有早早将你掐死,到如今反受你害!”
她骂着,想起前番被明玫那顿打,不由心口发疼,“你们夫妻蛇鼠一窝,一个出手殴打,一个使毒用一药,欺尊灭祖,枉顾伦长,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哈,你们等着,早晚都是天打雷劈报应!”
霍辰烨不为所动,天打雷劈也该先劈她吧。看着她那因激动而扭曲变形越发狰狞面孔,霍辰烨反而觉得这样好多了,至少比刚才那惺惺作态样儿让他舒坦多了。这样才正常嘛,才是今时今日大家该有态度嘛。
楚惜惜招认之后,霍侯爷怒不可遏,是他求了情。
她还是活着好,活着反思她罪过,活着享受她现状,比死了一了百了好。
他不想再和她多费口舌,转身向外走去。
霍侯夫人追后面,继续叫嚣道:“我要去告你们,去圣前告你们,你给我等着瞧好了。”
霍辰烨闻言冷笑一声,他停步转身,朝霍侯夫人走过来。霍侯夫人一惊,叫道:“怎么,你如今想灭口不成?我警告你,我有儿有女有一娘一家,你敢动我,他们知道了,绝饶不了你!”
霍辰烨笑了笑道:“我不灭口,我怕雷劈。不过,就算我灭了你,也不会让谁知道,别人知道了,也未必有心蘀你主持公道。因为你该死,你死了才是公道。至于见圣上,你还是别想了吧。你没看你连儿女都见不到么?楚姨一娘一招认后,父亲想问问灵姐儿烁哥儿意思,灵姐儿说,她是出嫁女,不好过问一娘一家事儿,只希望不要因你让合府蒙羞,便是她们出嫁女,也跟着难堪。你明白没有,她怕你带累她,让她婆家难做人。”
“烁哥儿,你知道烁哥儿做什么?他给你寻了一口棺材,很好材质,不过不太大。”霍辰烨说着,用手比划出一个匣子大小来,“你知道,你会‘传染’,所以焚化才保险。烁哥儿说早点儿备下,给你冲丧。另外,他提议了两次,说让炎妹妹早些也嫁,怕你忽然死了,妹妹守孝误了佳期。”
“至于贾家,你知道么,你家兄长和侄儿一起来看过你,就你挪到这里第二天时候。结果隔着院门儿看到了你满脸流黄水儿样子,恶心得你侄儿都吐了。我不过提了一句你这症状,和西南麻风村某些症状倒有一二份相像,你兄长就连声撇清,说你们家祖辈从来没有过这样病史。然后你兄长亲自劝父亲,说你这个样子,早些烧了,你也不受罪,亲邻也安生……”
霍侯夫人被霍辰烨话惊到,一副震惊惶然样子,她把手指放嘴里咬着,还哆索着嘴唇,含糊不清地道:“我不清,我不清……”儿女一娘一家都不能指望,那她如今还能指望谁?
她眼泪再次滚涌一出来,见霍辰烨又转身欲走,忙往前猛一冲过去,扑通一声跪下,哭道:“烨哥儿,我给你跪下,我知道错了,我不该那样对你,可千错万错,你也是我养大儿子呀……我求求你……”边说边又拉住了霍辰烨衣袖,然后手指迅速往霍辰烨手上一抹。
原本她刚才趁霍辰烨说话之际,把手指放嘴里咬破,如今血抹了霍辰烨一手背。她还试图低头去咬破霍辰烨手,被霍辰烨一挣一推,身一子就往后一仰歪到了一边儿。
霍辰烨看着被涂上血腥手背,冷冷看着她。
霍侯夫人却从地上站起来,拍了拍膝盖,扬声大笑起来:“哈哈哈,你给我换了药,你让我会传染?我就把我血涂你身上,你好落得我一样下场。哈哈哈,哈哈哈!让大家都看看,你和我一样……”说着又扬声长笑起来,状如疯魔,好像周围有许多观众,她宣扬她威风。
“你没想到吧,霍都督?我就是死,也要拉着你垫背!我有传染病,你却跑来看我笑话,不是天助我么?可见天谴你,让我蘀天灭了你!”然后,殊途同归,她烁哥儿还是侯爷唯一儿子。
霍辰烨脸色冰冷。他就知道,不该对毒蛇手软。
他冷冷扯掉刚才被拉过衣袖,1容手上血擦干净,然后转身大步出去,再没做片刻停留。【通知:请互相转告乐文小说网唯一地址为]院门再次紧闭起来,1容那狂如鬼魅般大笑掩门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