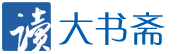他定定看她,缓缓道:“阿若,你不要装傻。”
“你觉得我应该如何反应?泣不成声地哀求‘你不要伤害我心’,还是喝下三瓮老醋,跳起来和你女人争周一到周末,你归属权?”美若扯扯嘴角,“这不是笑话吗?”
他表情僵滞。
“你明知道,我哪怕从了你一次二次,不代表我喜欢那种事,即便我喜欢上那种事,不代表我喜欢和你做那种事——”
“阿若,我心情不佳,不要激我脾气。”
她深呼吸。
轻声问:“你喜欢孩子吗?”
他认真思索片刻。“不知道。从没想过会有孩子。”
“拜托你们学着喜欢他一点吧。他出生前,你们没有征询过他同意。起码,他出世后,给他一点点关一爱一。”
他脸依旧僵如铁板。
“我回去了。”她想推门下车。
“阿若。”他不舍,拦住她去路。
美若笑,“你打算怎样?再次扒光我衣衫,把你那个脏东西塞我嘴里?我哭着说不要,然后该叫你什么,姐夫?契爷?不对,我弟弟妹妹父亲,那叫什么?继父?”
他闭紧眼,松开手。
美若恶毒地想,反正这世界都他一妈一疯了,她一妈一疯疯癫癫也是好事。
有詹美凤做挡箭牌,起码她能躲房里,获得少许清净。
年后何平安厨房里等她,面前摊开一堆表格。
“大圈哥给你找到学校,就同个区,上下学方便,师资也过得去。”
美若冷眼相睇。
“阿若,再怎么样,书还是要读。”
她知道混账打算,引蛇出洞,把她弄到外面去。
美若拒绝接受何平安递来笔。
“我厌倦了上学,上次庇理罗带给我深重一阴一影,我怕又有人半夜跳上我床,引得满警署差佬们上门抓一奸一,再向学校宣告我是J女。重来一次,我会崩溃。你可以这样向他汇报。”
何平安苦笑,“阿嫂……”
“你叫错人了。”美若指指楼顶。
“阿若,为将来计,你也该好好读书。就算我们九龙城寨穷鬼也清楚,只有读书好才能出头。”
为将来计,她该抓住大把钱银,即便去找四九叔过程里出了意料不到变故,她也能和七姑异乡生活下去。
“我生活费呢?救了他两次命,他说会照顾我生活。平安哥,你去告诉他,先把拖欠那几个月算清。”
过了几日,何平安带来几方现金。
再次把表格递给美若,“大圈哥有讲,签了这钱都给你。”
美若瞪他。
何平安无奈,添多一句:“大圈哥还讲,签不签生活费也都给你,就是会粗一鲁些,开学那日亲自绑你去。”
美若开始填表。
学校就油尖旺区,美若既来之则安之,努力扮演好学生角色。
头一天下课,蔡炳谦守候校门。
“蔡督察,你是来向我说对不起?”
她笑颜如花,细一嫩皮肤光泽彷如拨一开了铅色云,蔡炳谦为之失神,但话语里嘲弄和轻鄙又将他拉回现实。
“我是为了再次让你明白处境危险。”
每个人都说为她好,真正为她好,大约只有七姑。
美若连“呵呵”两字也欠奉。
“詹小一姐……”
蔡炳谦被人楸住衣领,顶围墙上。
“詹小一姐没空。”
蔡炳谦也是经过事人,与充满威胁意味双眼对视,他毫不惊慌。“和兴大圈哥,你知道袭警后果。”
靳正雷狞笑,“我不敢,我好怕。我动你一个手指头会坐半年监,怕得尿裤裆。不过,蔡督察,你由石头缝里跳出来?没有六亲?我记得,你有老婆,听说五官颇端正,还有个儿子就读东区幼稚园,好像还有个同胞姐姐,没你老婆端正,总也算个女人。”
蔡炳谦脸色微白。
“我忍你很久了!今日起,宁波街上和我阿若周围五十米内,我不想再见到你。”
他放开蔡炳谦,嫌恶地拍拍手心,将静静立一旁美若拥进怀中。“阿若,回家。”
蔡炳谦身后咆哮:“你会后悔你今日说每一个字!”
靳正雷送美若上车,回过头来,笑得格外开心,“我等你。”
“他属纪律部队,执法队伍。”
“我不会给他机会。”靳正雷凑近她冷冰冰小一脸,“阿若关心我?”
她认真点头,“弟弟妹妹需要一奶一粉钱。”
“我已经解释过,是不是我种只有她明白。”
“这和我无关。”
他沉下脸,片刻后重重一脚,踹向前座座椅。
美若无动于衷。
“就不能谈些别?学校喜不喜欢?有没有有趣同学?第一天是否习惯?”
“不喜欢不讨厌,没有有趣同学,很习惯。”
靳正雷往后靠,许久不开口。
直到司机回望,他无奈挥手:“去吃饭。”
连镛记伙计也熟识她,一口一个“阿嫂”,美若置若罔闻,喝茶等上菜。
“阿若,下半年,我筹点钱,另买一间屋,给你搬出去住可好?”
记得当年华老虎看上警署隔壁书店老板一娘一,后闹大了,用浅水湾一套别墅摆平家中母老虎。
美若笑一笑,转移话题道:“你事业展如此顺利?”
“还行,大家给面子。”
“那惨了,有朝一日你达,我们母女将会沦为全港笑一柄一。”
他狠狠剐她一眼,而后转头给自己斟酒。
镛记出来,美若知道靳正雷将会带她回哪里。
车停观塘他老巢楼下,她拒不下车。
“阿若,你要我抱你?”他探头进来问。
“像第一次那样?”美若从书包里拿出他五四式。“你试试。”
他一抽一一口凉气。
她冷静地拉下保险阀,正正指住他胸口,同时吩咐司机和何平安:“滚下去!”
靳正雷下颚收紧,目光从那黑一洞一洞一枪一口,移到她冷冰冰小一脸上。高悬霓虹灯,她身上和身后车窗玻璃上,反射一出迷幻光。
这一刻,她美得炫目。
“阿若。”靳正雷几乎要将她看进心里去。“我亲过你,摸过你,和你躺一张床上,睡过不止一觉。你居然手也不抖。”
她抿紧嘴。
“阿若,会炸膛。”
“炸膛,大不了我死,不炸膛你死。我们来赌一赌,谁命大。”
他背光,看不太清面上表情,但一双眼如风暴前深海,美若能感觉到其中无形压力,她握紧双手。
良久,他才一字一顿地说道:“我赌不起,我认输。”
瞬间,她几乎软一了手脚。
“阿若,你想怎样?”
“我想你不再碰我,再有下次,还是一样。你知道还有三子弹,总有一颗能了结你我一性一命。”
她用一枪一指指他,“叫欧伯来,开车送我回家。”
视野中,靳正雷伫立街头高大身影渐渐消失,美若这才收回他一枪一。
“小一姐,你这样不对。”平常只会说“是、对、好”欧伯居然开口。
美若警惕地望向他。
“男人我懂,越得不到越是好。九龙城寨八婆我见得多,拎锅铲打老公不是没有,但是,玩一枪一女人……”欧伯摇头,叹为观止地啧嘴,“换我做后生那阵,我也不会轻易放过。看架势也知,一操一起来很给劲。”
混账王八蛋,请个司机也是退休黑社会。
美若一枪一不离身,睡觉枕头下,上学藏书包。
她用心防范人却彻底于她世界消失,只有何平安,接到詹美凤电召后,会来宁波街给詹家送上补给。
詹美凤显怀后,脾气格外暴躁,家里佣人隔三岔五换人,时时有面孔。
詹笑棠倒经常来,笑嘻嘻找美若说话。可那笑容背后,美若分明感觉藏了些让她恶心目。
她回家就躲进厨房或者小房间,那是她为自己规划活动场地。
那个人唯有一样优点,不会空口许诺。夏天时候,他掷千金,买下半山一栋白色洋房。
詹美凤再也不喊腰酸背疼咪咪痒,笑吟吟,摸一着隆一起肚子,一精一神抖擞地指挥佣人置办家。
居景致不错,能望见一部分海和中环,三层,附带地下酒窖。
詹美凤从自家平治上下来,看那部车格外不顺眼,恨恨道:“起码要换部劳斯才衬得起。”
到了露台望见海,她才喜笑颜开,眯眼吸一口鲜空气,得意地对詹笑棠道:“家姊这步棋没走错吧。”
詹笑棠连连点头,谄媚道:“家姊一精一明。”
又问道:“他今日不过来?”
詹美凤顿时一阴一了脸,“管他来不来,你这么想见他你只管去。”
见弟弟讪讪,她问:“听说近他又跟谭笑搞一起,是不是,笑棠?”
“这些风花雪月,哪个男人不沾点?”詹笑棠安慰道。
“我挺个大肚,没功夫理。也好,”詹美凤眼角扫向楼下,美若房间窗户。“偷食只要不偷到家里,我当看不见。”
她抚一摸肚皮,“宝宝,就看你表现了。你争气,阿一妈一等你长大,带你住山顶去。”
八月时候,詹美凤二楼叫得撕心裂肺,七姑想送她入院,她拼死不肯,只是凄厉地吼:“打电话给他,叫他来看看,我为他付出多少。”
七姑知道她一抽一筋难受,按摩一下便好,但大小一姐坚持,她唯有打电话给平安,苦苦哀求。
靳正雷来时,天色将晚。
将詹美凤送上车,他站门廊下回望。
美若见藏不住,从门后走出来。
半年多不见,她高了些,下巴尖尖眼大大,嘴唇像门廊下那株浸过雨水玫瑰花一瓣。
他胸口一紧同时,忆起于那两片唇一瓣上掠过滋味。
“她很辛苦,我半夜听见她楼上哭。”
“你半夜还不睡?”他问。
她低下头,注视自己鞋尖。
他张口想喊“阿若”,随即紧闭上嘴,转身下了门廊,手下簇拥中分几部车离开。
作者有话要说:下次:明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