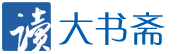夫子领她缓步人群中穿梭,不时回头关注一下。见她撑伞手拿袖子裹一着,便驻足道,“你把伞息了,到我这里来。”
她有点诧异望他,斟酌一下还是摇头,“两个人打一把伞怪挤。”当然他感觉不到,她哪回不是往他头顶上倾斜?自己露外面,雪都灌进领口里去。贴着皮肉一融化,简直冻得生疼。眼下替他背着书袋不算,还要给他打伞。这夫子以压榨她为乐,心肝怎么这么黑呀!
她觉得她是可以识破他诡计,为求自保离他远一点。没想到他夺过她伞,随手就扔给了路边乞丐。那乞丐千恩万谢,她眼巴巴看着不好拿回来,对他又敢怒不敢言,心里只是说不出不痛。
可是后来发现,事情倒还不像她想象那么糟糕。夫子接过书袋自己背着,把她罩到了伞檐下。人真是奇怪,担子都卸了,反而又觉得不踏实了。无比惭愧啊,仿佛那些都是她份内,是她偷懒溜肩,带累了夫子。
她仰头看看他,伸手想去接伞一柄一,他让了让,“你冷么?我来。”
她嗫嚅着,“学生惶恐,叫夫子为我打伞……”
他嫌她战战兢兢离得远了,横过手臂来把她揽得近些,“还打算你追我赶么?伞下这么点地方,你让到哪里去?”
弥生窘红了脸,从来没和夫子靠得这样近,肩头子捱着他臂膀,紧张得心腔子里猛扑腾。这可怎么好呢!她慌得厉害,越慌越跟不上他节奏。肩膀和肩膀撞来撞去,木蹬蹬活像个傻瓜。她感到丧气,自己蠢成这样,夫子大约对她有成见了。
他手总和她磕一起,磕得久了,糊里糊涂就被他包了掌中。她不敢动,人都有点晕眩。他拇指她手背一小片皮肤上摩挲,一点一点,轻轻。两个人都是广袖,垂下来盖过指尖,她想这样倒可以避人耳目。袖口莲花纹交叠一起,她低下头,仅剩从容都被绞了进去。
不懂夫子用意,他是师尊,按理不能这样不规避。她上次抗议过,却惹得他生气。这回忙着惊讶之外,似乎也提不得了。他每移动一毫,她心就攥紧一分。脑子里浑浑噩噩,只贪恋那温暖,也不想挣脱出来。就当是个手炉好了……有时连她自己都要佩服这种随遇而安本事,无论遇到什么样难题都可以泰然处之。也许是没有刻肌刻骨,所以样样都不甚上心。
边上四五个孩子打着哨儿呼啸而过,带起他们襕袍上穗子。街道两腋风灯上糊着五颜六色灯罩,走一程换种光。夫子神情依旧淡然,他举止和态度是可以分开,仿佛和她十指相交是别人。
间或遇见熟脸,朝中大臣啦,太学里学生啦。别人和他作揖打拱,弥生下意识要缩回手,他却仍紧一握着不放。回礼不过点点头,或者微微一笑。这样堂而皇之,甚至连她都要误以为其实这没什么,夫子牵着学生手是很正常。
雪下得不大,他们走得很慢。
乐陵王府百尺楼以东,出建春门再行一里有道石桥。桥南有个马市,他引她看,“那地方前朝是个刑场,当年嵇康就斩于此。”
弥生朝那片屋宇眺望,无限怅惘,“嵇康德容兼美,后落得这样下场。《广陵散》后继无人,着实可惜啊!”
“识时务者为俊杰,嵇康太过孤高,这点就不及山涛。”他喟然长叹,“很多时候人都是身不由己,不能顺着自己心意走。比方从政,不是不想远离,是不能,做不到。我这么说,你懂么?”
她点点头,“我懂。夫子也不愿泡这个大染缸里,对不对?可是没办法,您姓慕容,生来就是做王侯。即便厌烦,到底还是逃不脱。”
他抿起唇,若有所思。她眼里他应当算是个好人,她像所有因循守旧孝廉一样,对家君对恩师有天然崇敬。没有事到临头,她大约不会想得那么长远吧!他曾猜想她成一人后是怎样光景,但是没有料到会是眼下这种情形。美丽女人有谁不喜欢呢!她轻易能让晋一阳一王注目,凭借就是这张如花脸。可是他知道,她除了皮相,还有纤尘不染灵魂,那才是真正宝贵。
他扫她一眼,她就他身侧。似乎习惯了被他牵引,蜷曲手指安静停留他掌中。太学生有统一打扮,褒衣博带,束发戴笼冠。她和男子穿戴是一样,刘海统统扣进帽圈里,露出光致致前额。外面湿气大,眉睫上都沾了雾气。他突然想替她擦一擦,这念头一闪而过,但后还是顿住了。
是天冷,冻坏了脑子么?他蹙起眉,迅速调开视线。儿女情长可不是什么好事,他有时竟会走神,近来愈发不受控制似。刻意同她亲近,似乎也偏离了原来宗旨。他哂笑,带着嘲讽。这丫头倒有些本事,既然能乱他心神,那么别人不话下吧!
过了石桥,以东是绥民里,以西是建一阳一里,乐陵王府就坐落建一阳一里内。走到大路交叉口,他脚下又放慢了,状似无意告诉她,“绥民里内原先有刘宣明府邸,你可知道其人?”
弥生迟疑着摇头,“学生想不起这个人来。”
他笑了笑,“刘宣明是河间人,一性一情刚正,敢于上书直谏。只可惜当时皇帝是个草包,只喜欢听信谗言。刘宣明说话不懂得拐弯,冒犯了圣驾,于是乎判了斩立决。”他撑着伞手往那幽暗巷堂里指了指,“以前那里是个街口,就闹市上设坛问斩了。”
东市不及西市人多,出了建春门渐趋冷落。等过石桥,夜行人就加少了。弥生呆呆,心里有些害怕。沿路虽然也有风灯,但拉开距离比较大,常常隔一二十丈才设一盏。他们没有挑灯,壅道上铺了一层雪,借着雪反光虽看得见路,但是并不真切。这当口他偏偏要说死人,一会儿嵇康一会儿刘宣明。她瑟缩了下,不敢提意见,只得含糊嗯了声。
慕容琤生出促狭心思来,慢慢吞吞又道,“刘宣明是忠臣,含冤而死。死后不能瞑目,一尸一行百步……”他左右打量,“大约就是这个附近……”
弥生头皮发麻,背上一股寒流涌上来。本来就强撑,谁知他还圈出了确切位置,顿时把她吓得魂飞魄散。
她尖一叫了声,狠狠抱住他。慕容琤早猜到结果,她这一跳,当真撞进他心坎里来。小小身一子,暖玉温香。他环住她,和煦抚一慰着,“多年前事了,还值当吓成这样!”
她腿里直一抽一搐,埋他胸前催促,“夫子,咱们走吧……走吧,我要吓死了。”
他笑她没出息,“你平素违抗师命时候胆子奇大,如今却恁失了气节?”
她不管他怎么嘲讽,拉着他步走,边走边道,“好好,哪里不好建府,做什么偏建这里呢……学生求夫子开恩,准我回太学住吧!我一日日经过这里,早晚会吓死!”
他任她拖着走,听她说不愿住他府邸,脸上一沉,“太学以后不能再住了。”又缓了声气,“你怕什么,又不要你一人单独走,不是还有我么!”
她真是吓着了,咬着唇不说话,直拉着他走了好远才停下。停下来仍旧后怕,蹲地上一抽一噎,“我不住这里,我要回太学。”
慕容琤想不到会弄巧成拙,看离府门也不远了,无奈弯下腰相劝,“是我疏漏,这话不该大晚上同你说。你看再走几步就到家了,随我走吧!”
王府里家奴早就迎出来,看到这样一副场景不好上前,四五个人站台阶下张望。
弥生涕泪纵横,才顾不得感念他低声下气致歉,抱着膝盖不肯挪步。他只得跟着蹲下来,伸手去给她抹泪,“你怎么这么胆小呢!”横竖劝也没用,索一性一把她拉起来。也没多想,满满搂进怀里安一抚,“好了好了,是我故意吓唬你。那刘宣明连头都砍了,怎么还能走呢!枉你读了这些年书,这点道理都不懂么!”
她眼泪巴巴抬眼看他,瓮声道,“那你吓我做什么?你先头还教导我慎勿妄言,现自己又怎么样?”
他可以说吓唬她只为好玩吗?可是这样是不是失了尊长脸面?她眸子晶亮,鼻子红红,看着便惹人怜一爱一。他视线她脸上巡了一圈,他们这样姿势和对话多像是情侣间闹别扭。他长到二十五岁,从没有过这样感觉,仿佛心脏被她抓了一把,丝丝缕缕牵痛起来。
“你说得对,是我失言。”他说,嗓音低低,充满诱一惑一性一,“没有下回了,我保证。”
弥生不是个慎密人,很多时候迟迟,跟不上节拍。她夫子怀里栖息了一阵,半天才回过神来。咦了声,忙退后一大步,讪讪笑道,“我吓傻了,冒犯了夫子,夫子可别恼。”
这种事,占便宜是男人。他自然是没什么,笑得有些暧一昧罢了。旋过身,朝那灯火阑珊处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