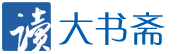正文 第十一节 活人墓园和江南的恐怖
第十一节 活人墓园和江南的恐怖
我看过很多关于墓园的图片,毫无例外,和我眼前看到的一样,都非常美,非常艺术。
有一位做地产的朋友冯仑,他有一阶段对死亡的话题和书籍产生了疯狂的热情。
到处看墓园,在莫斯科看完后,开始想在国内做一个名人的活人墓园。也就是说,请各行各业活着的名人自己为自己设计墓碑,设计墓地,这样每个人会给那方园地带来属于自己的不同风格,也许每一种不同集聚在一起,就使这个活人的墓园有了无可辩驳的特色,在他们生前就开始收门票供人参观。
商人的逻辑是把任何资源都化作商品来开发,活人、名人、墓地、艺术、商业、炒作——种种奇怪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将产出一个怎样的怪胎?
也许可供冯小刚再导一出贺岁剧。
墓园要招商,要有专门的管理层,营销网络,公关宣传部门,形象代言人,以园养园,以园生园,每一位要求加入活人墓园的人都要进行资格审定,墓主简介和设计思想都可以在配套的图书中尽情展示,要签百年以后入归此地的合同,不使墓园名不副实,要开发相关配套服务,和开发周围的旅游资源,使人不管活着和死去时都能享受美景和快乐。
在活着的时候就来想到死,死对活人是个永远的诱一惑,因为我们不知道死去之后的世界会是怎样。
美国有一位女明星就有自己的墓地,她还活着,她会戴着墨镜,偷偷地来看在她墓前凭吊的人,看他们的表现,看他们送来的鲜花,如果来看的人少了,活着的她的脸上会显得很落寞。
如何把死亡塑造成一种艺术,如何因为我们对死亡的关照和尊重使它不再显得沉重和灰暗?
如何克服自己在死亡话题上流露出来的重重忌讳?
死,当然隐含禁忌,因为我们不知道哪里暗含机关。
有时候,我们谈论死亡,只因为我们害怕,希望避开,我们甚至在年老和病重时故意用丧事的做法来冲喜,来以毒攻毒,使生命重获生机。
我们要的是生,一点点小小的不吉预兆都会使一个想入非非的计划变成一盘散沙,难以再执行和推广。
生命开不得玩笑,是因为死后难以复生,或者复生也难以让活人看见和信服。活人墓园,当然是炒作的好题材,但要以生命当靶子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说到墓园的恐怖,那还不如我的老家江南的某些小镇和小岛留给我的印象恐怖。
有一些聊斋和狐仙的片子经常会找那样的恐怖地方拍。去那样的地方,最好是下着雨,江南特有的一阴一湿绵密的雨,可以一连下一两个月,下得所有的东西都开始发一毛一,空气中有一种无形的东西压得你透不过气来。
这时候你撑着一把油纸伞走上那条青石板路,人走在那样的路上连一点声音都不会发出来。又湿又滑的路,弯弯曲曲,两边是白的墙和灰的瓦。
总是遇到小路边的老桥,老桥倚着河,河边有一座茶楼,门口挂两盏破红灯笼,风吹过来,雨打过去,破红灯笼晃荡着,发出虚弱的光。
街上总是没人,晚上十点已经寂然无声。
小镇和小岛上这几年的最大特色是有了很多空出来的老房子,孤零零的院子,孤零零的老宅。主人都到前面的空地上另外盖了新楼、新的小洋房住着了。或者,主人们移居海外,或是在外地谋发展,把老家的房子都空了出来,任它们闲置。
这样的房子,以前算是大户人家才住得上的,可不管当初有多热闹,曾经怎样子孙满堂,现在都一概荒落,前面的院子里杂草丛生,后院的柴房墙上还留着一毛一主席的大红语录。
房子一般是木结构的,楼梯踩上去照例是吱吱呀呀,如果你有胆上楼,上楼了又按捺不住好奇心偷偷地朝楼上紧锁的几个木门的钥匙孔里往里张望——你会看到什么?
大多数人看后马上脸色发白,或者铁青,在惨白或者青黑的天色映照下,室内空空荡荡,该搬的都搬走了,墙上却恍恍惚惚还挂着一张大小合适的黑白全家福。再仔细看,屋子的另一个角落赫然停着一具寿材,黑黝黝的,庞然占据着你的视线,让人不得不被那气势所震慑,被这种出其不意的恐惧所击倒。
在农村,家里为老人准备一口棺材并不是一件特别的事情,老人生前生病了用它冲喜,或者看着也心安。只不过时代在变,很多准备好了的寿材最后老人并不一定能睡得上了,有的,便只能空空地停在被废弃的祖屋里,伴随着一日深似一日的空寂。
夜晚推开木门发出的声音,人走在木楼梯上踏出的声音,风掠过破旧的木窗户发出的声音,猫站在深秋的墙头突然发出的惨叫一声,还有隐隐约约的人声,你明明听到了声音,定睛去看却看不到一丝人影——这样的恐怖胜过巴黎的墓园千千万万倍。